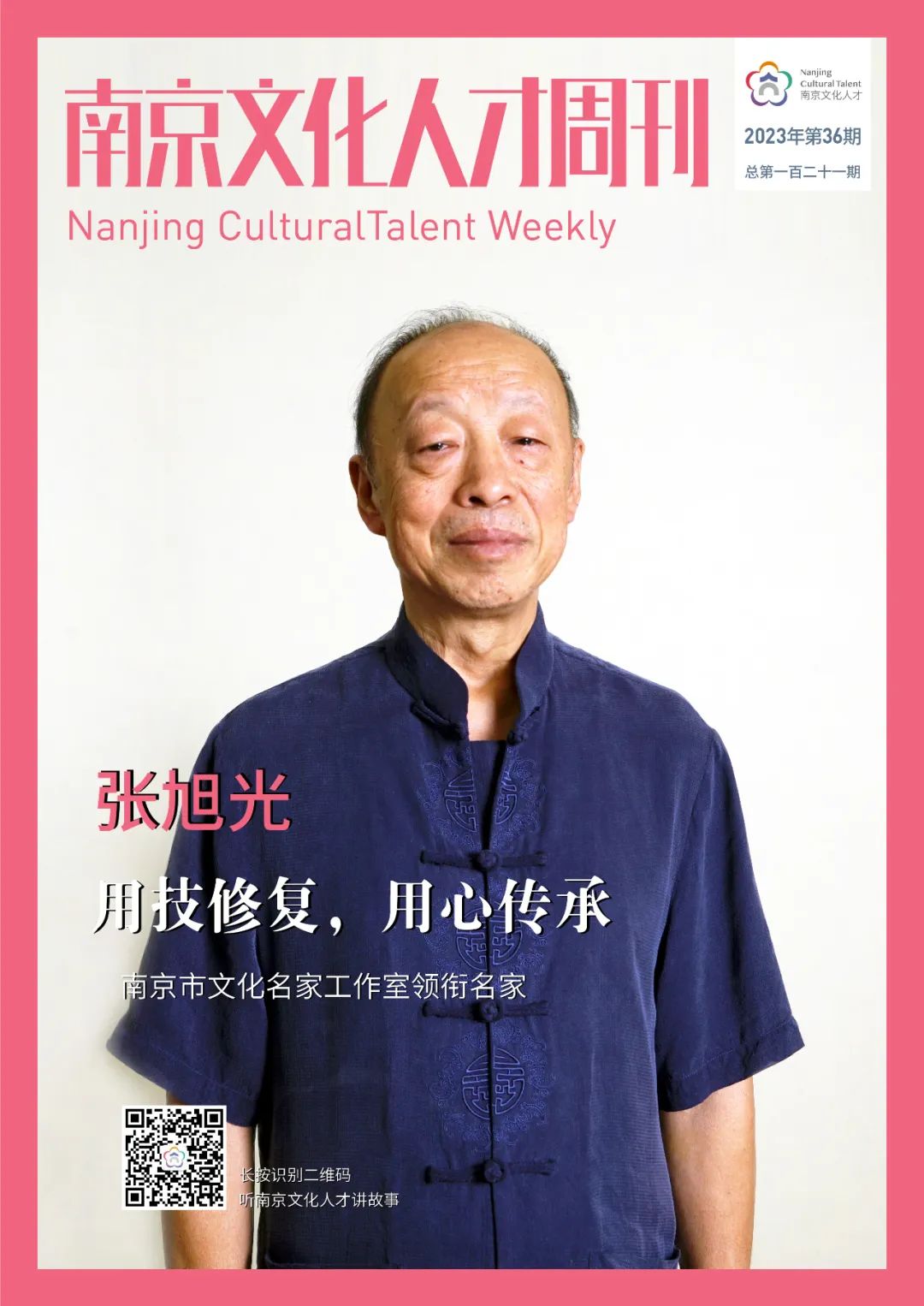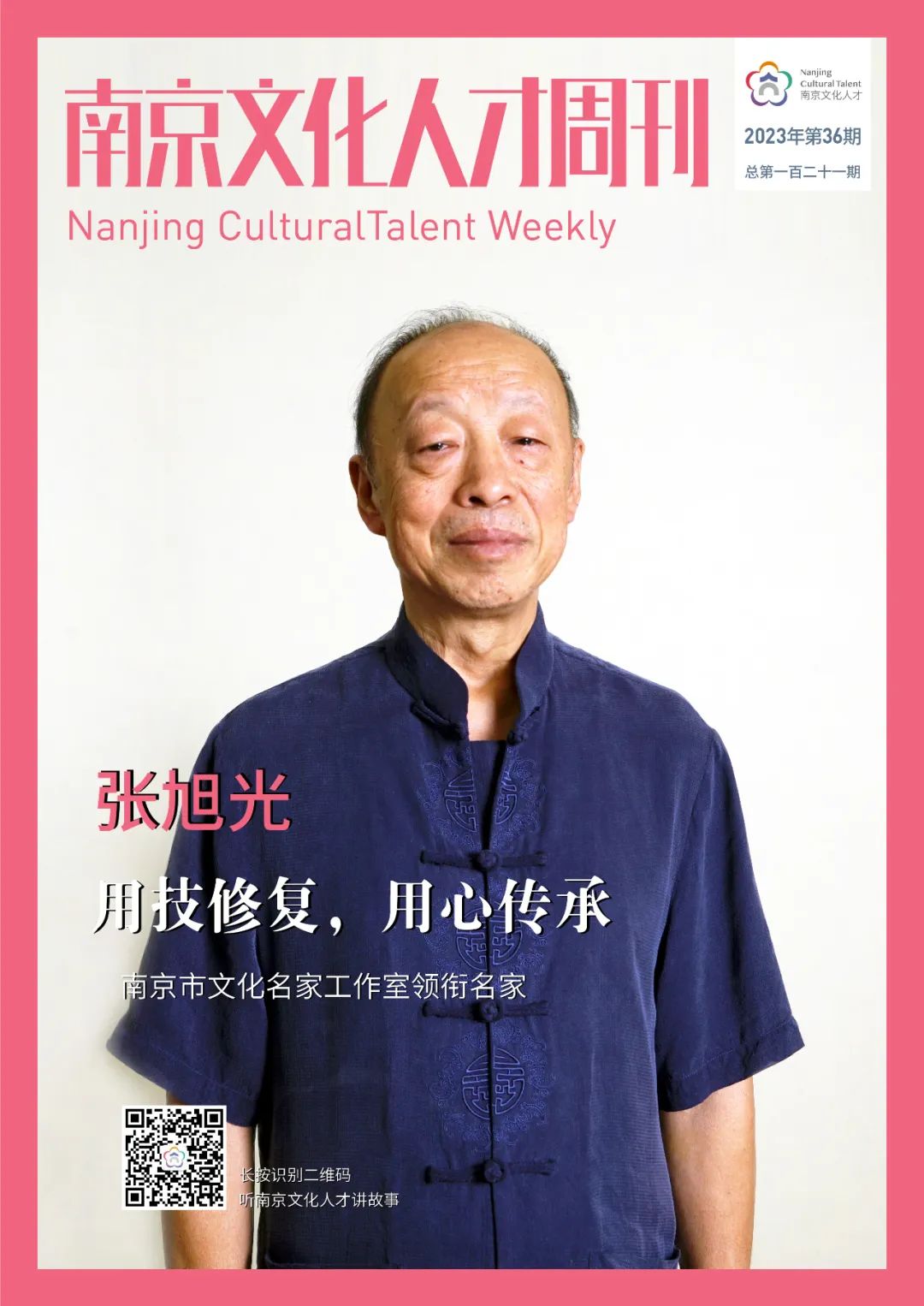
张旭光
南京市文化名家工作室领衔名家
“修复这门手艺不属于我们任何一个人,如果这么好的技艺不让年轻人知道,不仅对不起后面的‘来者’,更对不起前面的‘古人’。”
——2023年第36期
每一件文物的呈现于世,离不开一代代考古工作者“手铲释天书”的接力传承,也离不开一代代文物保护者“甘坐冷板凳”的悉心呵护。
故宫书画修复大师、装裱修复技艺(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传承人张旭光便是其中之一。
早已退休、常年定居北京的他,仍然定期赶到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院,以下简称“南京非遗学院”)参与书画修复技艺教学工作。那里也是南京市文化名家工作室——张旭光工作室的所在地。学生们从张老师手中接过修复技艺的“薪火”,也接过文明传承的“火把”。
修复凭巧手 琢磨靠巧心
乒乓球桌大小的工作台上,张旭光用一双干瘦、粗糙的手在待修复的画卷上轻轻地搓着。一个又一个纤细如火柴棍的小纸卷魔术般从他的手中滑落,这便是古书画修复“绝活”之一:搓揭。
古书画一般分四层,一层画芯、一层托心纸、两层背纸。古书画修复之前要先揭裱,难点在于将最薄的一层宣纸画芯分离出来,这样才能在修复之后重新装裱。
画芯通常只有0.09毫米,薄如蝉翼。揭裱的时候稍一点儿抖动,就可能揭“残”,一幅珍贵的画卷就毁了。搓揭,靠的是手感,张旭光的一双巧手,已经练到“出神入化”,这背后,是近40个春秋磨砺,上万次的苦练。
 张旭光(右)在工作中
张旭光(右)在工作中
做书画修复,讲究一个“巧”字。不仅手要巧,心更要巧。
“文物修复的魅力就在于,没有两件文物的情况是一样的,就像人得病,外表看症状一模一样,但是造成病害的原因可能各有不同,因此,修复的方法、采用的材料及工艺等,各有不同。”张旭光说。
2005年,一张《明代正统皇帝圣旨》被送到他手上。
这件甘肃省张掖市博物馆馆藏的圣旨,除了通体残缺断裂,存在霉斑、缺字等情况,背面采用的还是撒金双面蜡笺纸。由于在清朝中后期采用这种材质加工的工艺就已逐渐失传,这道等级极高的圣旨一直无法修复,被深藏于库房中。
“要想弄清蜡笺纸的加工工艺,首先要搞清蜡笺纸的纸基用的是什么纸,是否是传统的宣纸;其次,必须弄清楚其表面涂层的成分;最后,研究古人如何将蜡均匀地涂布于纸基表面。”
张旭光又琢磨上了。
他和同事去库房查看了现藏清代蜡笺纸,发现其正反两面均涂以蜡质,颜色有明黄、橘红、淡蓝、浅绿、粉红及白色等。而在样品表面上取样时,他们又发现蜡与纸张之间还有一层未知的粉状物存在。
张旭光和同事专门到北京化工大学化学分析中心对蜡笺纸表面物质进行分析检测,还千里迢迢跑到蜡笺纸故乡安徽省宣城市泾县做调研,找老师傅取经。回到北京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进行试制。
为了能最大程度地还原蜡笺纸,张旭光在用料和制作手法上都尽量遵循古法,同时也进行了创新。比如,在实地调研时,当地的老师傅曾告诉他们需要用人的头发蘸蜡、上蜡,试制时张旭光选用猪鬃刷代替,并参考擦漆技艺,采用八字法、圆圈法上蜡。最终,他们不仅试制成功,还配出原圣旨失传已久的明黄色。
尽管修复一道圣旨花费了一年的时间,但每每被问及其中的艰辛时,张旭光总是以一句“就琢磨呗”轻松带过。
历史虽无名 技艺有传承
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科技部位于故宫西华门内的一座安静院落。装裱科的办公室砖瓦都是灰色的,屋顶也没有色彩鲜艳的琉璃瓦。这里曾经是清朝遗妃们养老的住所,退休前,张旭光一直在这里工作,遵从本心,无问西东。
“做修复的和绘画不同,没有落款和署名,但能在历史的背后做一个无名的参与者,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张旭光说。
出生在装裱世家的张旭光,一家三代都是裱画人、修复师,从外祖父刘定之到父亲张耀选,最后,张旭光也选择了子承父业。
刘定之是书画装裱修复大师,在苏州、上海两地闻名。他先在苏州开了一家“晋直斋装池”的裱画店,后来又到上海开了“刘定之装池”店。1960年,刘定之进入上海博物馆文物修复工场裱画组任技术顾问。
因为心灵手巧悟性高,祖父将毕生的手艺和绝活传给了父亲张耀选。1954年,应国家文物局邀请,张耀选带领一行5人到故宫博物院从事古旧书画的修复工作,并将装裱的精湛技艺传到了故宫博物院。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古书画修复的开创者,担任故宫书画修复组第一任组长,在故宫工作的25年间,张耀选修复了几百件书画文物。
1986年,20多岁的张旭光承袭了父亲的手艺,进故宫接班。单位其他部门的同事中很多人不知道他和张耀选先生的关系,上两代传承到张旭光手中的,没有名家子弟的光环,只有精湛的手艺、匠人的风骨和传承的使命。
 工作中的张旭光
工作中的张旭光
在民间手艺人中,有“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说法。
张旭光的父亲却从不保守。“他教给徒弟的,比教给我的还多。我知道,他希望学生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张旭光也是如此,对于学生,他从来都是倾囊相授,还把研究过程和科研成果写成论文,对外公开。
“修复这门手艺不属于我们任何一个人,如果这么好的技艺不让年轻人知道,不仅对不起后面的‘来者’,更对不起前面的‘古人’。”
接力传后辈 文化再焕新
在工作室中,张旭光虽是个不苟言笑的严师,但他对学生却从不藏着掖着。即使是教染纸,也要从调色起,铺纸、裁纸、染色、上墙,带着学生一步一步做。
只要学生对修复过程有疑问,无论是口头询问还是发信息,他都会认真斟酌及时回复。做书画修复的,因为老是站着,腿和膝盖会疼。但即便如此,在工作期间,他也会来回转,尽力照顾到每一个成员,一天下来,稳稳占据步数排行榜前列。他原先身材略有点胖,2013年带过一个十几个学生的培训班,结果3个月体重下降了9公斤。即使遇到不能亲临现场的情况,张旭光也会进行线上书画修复教学活动。
跟父亲学艺时,张旭光常听父亲讲“咱们这一行,就是干到老学到老”。而他将工作室的传道授业解惑视为学习的途径之一,“我也是在不断‘修复’自己的‘盲区’。”
“张旭光工作室”成立后,南京非遗学院文物修复中心承接了27件贵州省博物馆文物、2件盐城市博物馆文物、60件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文物、18件南京工业大学文物,以及大量红色文献、书画、地图的修复任务。
每每遇到等级较高或破损严重的文物,张旭光都要亲自主持修复工作。而每次修复,他都尽量把“上手”的机会留给工作室的成员,自己则从旁指点。
 工作室成员在认真修复文物
工作室成员在认真修复文物
工作室曾经接手过一份绢本《重彩如来佛像画轴》。画芯采用了薄如蝉翼的网绢,上面还存在大量难以清洗的霉菌。而原来的“命纸”(绢本书画装裱后,紧贴绢背的一层纸,对保护画面有密切关系,犹如书画的性命一样重要)不仅被揭过而且损伤了画意,颜料也粘黏在命纸上。
绢本在古字画修复中本身难度较高,加之其画轴尺幅较大,长宽都在1米左右。画轴还存在大面积断裂、缺损、污渍、裱件脱层等情况,几乎是“千疮百孔”。
这些都为修复工作带来巨大挑战。
张旭光带领工作室成员借助仪器设备,对文物的pH值、色度、污染物类型、写印色料和造纸纤维等指标彻底“体检”。但之后清洗、揭背、托芯、隐补、全色的过程则全部依靠手工。
张旭光介绍,面对密集的小洞,本可以用整幅绢托在画作后面,一下把所有的洞都补上。这样的修复方法虽说简单省事,但对文物后期保护不利,长时间下来绢与绢之间容易分离。为了延续古画生命,他们选择采用小面积补绢,然后用纸张托画芯,避免后期空鼓的可能。
画芯修复完成后,张旭光又与南京非遗学院老师,原南京博物院馆员、文保所专职古旧书画修复装裱师万董强一道,完成了画卷的“托芯”,并认真细致地教学员如何对缺笔、掉色的细节进行修复。
修复背后是艰难且漫长的攻关奋斗,但提及过程,张旭光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修复靠大家群策群力完成,真正的功劳并不属于我,而是属于那些年轻人”。
在他的带领下,工作室每年还会定期举办非遗体验活动,让更多人了解这项技艺。
经常有人问张旭光,“您修复过最有价值的书画是哪幅?”
“书画的修复,取决于作品的受损状态,而不是文物等级的高低。每件在我手中修复的文物,对我而言,都价值非凡。”这位老人慢条斯理地说。
记者|张甜甜 编辑|芮天舒 排版|王 婧
剪辑|胡欣玥 美编|鲜曼青 校对|熊向宁